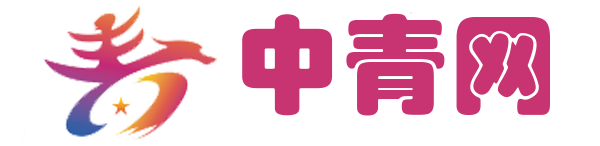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在《山行》中描绘的,于高山之巅偶遇几户人家的情景。在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的大寨顶,69岁的赵廷海,已在悬崖峭壁之上、缕缕炊烟萦绕的山巅独自生活了19年。
他为何独自留守?又是如何工作生活的?8月14日,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来到海拔768米的大寨顶,探访了老赵的“归园田居”。

海拔768米的坚守
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大寨村位于麻峪村南,海拔768米,是名副其实的大山之巅的小山村。《续修博山县志》记载:“大寨,县东南七十五里,周十余里,峭壁悬崖,陈疃乡附近避乱处也。”
古时,当地居民为躲避战乱和匪祸,在山顶建房扎寨,其险峻可想而知。
大寨村整体呈东西走向,面积虽大,但人口稀少。据记载,村子原有23户人家,108口人,分属张、王、李、赵、冯、谢、孟、焦八姓,村民几乎分散居住在方圆5里的山上。大寨东部和北部地势舒缓,四周却是四五十米高的悬崖峭壁,无人敢攀登。上山路有四条:一条从珍珠村南的大岭上攀4公里至大寨北门;一条从麻峪村北的小山脊(麻峪三叉岭)攀2公里至北门;第三条从池上镇陈疃村的盘山小路直通大寨南门,坡陡崖高,约3公里至山顶;第四条从池上镇后峪村沟底至“耩沟”,经崎岖林荫小路直通大寨顶。
可想当年,大寨村人最大的困难便是交通不便。传言,村民抱上山的猪崽、羊崽长大后因运不下山,只能宰杀后出村。因四周峭壁险峻,无法修路,生活和交通极为不便。1987年5月,博山区政府决定整体搬迁大寨村。
村民离去,房屋坍塌,茅草遮蔽小路,大寨村似将消失……但有一人留了下来,他就是赵廷海。


赵廷海,69岁,人称老赵。他是国企退休员工,2006年退休后,接替73岁的父亲来到大寨顶,修缮石房,安营扎寨,守护这片山林,一守便是19年。
一村一屋一人
如今的大寨村,仅剩老赵一人。记者一行从源泉镇麻峪村北面山脊开始攀登。夏秋之交,茂盛杂草掩盖了羊肠小路,行走艰难。历经近1小时,终见大寨北门石墙的残垣断壁。原先的石墙已难辨模样,仅余几处石头堆积,无声诉说着这里曾是北门。

前行中,一块镌刻“大寨”二字的村碑立于路边山坡。老赵介绍,2019年,几名登山爱好者出资立此碑。从此,大寨顶便有了这一村一屋一人的景象。
为何留守?老赵说,大寨3平方公里的山林是他永远的牵挂。父辈承包这片山林,看护一辈子,至73岁才下山。自接替父亲,他便与这片山林融为一体。
“这是我随身携带的小包,内有剪子、小锯,巡查时修剪不规则树木。”老赵展示工具,对山林的热爱溢于言表。十几年间,他精心呵护,山上仅槐树就有几十万棵,木材树和果树不计其数,树木覆盖率极高。



护林工作还包括制止乱砍滥伐。每当发现私自砍伐者,老赵虽遭谩骂推搡,仍坚定履职:“只要他们不再砍伐,就无妨。树木是国家的资源,我代表国家看山护林,我也不怕他们。”
春天防火关键期,老赵每日在7公里护林路上巡查两趟,提醒驴友勿带火种,查看是否有村民烧荒;夏秋时节,他修剪树木,种菜养鸡,过着田园生活;冬夜,听山林“虎啸龙吟”,亦能安然入睡。
日子清苦,老赵自得其乐。
高山之巅 老赵会一直在
为为了让山上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勤劳的老赵不停地改善着山上的环境。他一点点修整了从大寨北门到石屋的道路,从仅容一人步行通过到可以推着小车运输物资;他在自己石屋的周围搭起了凉棚、摆下了石椅石桌,供路过的驴友休息;他修整了周边废弃的石屋,养鸡养羊、种瓜种豆,生活自给自足。



收获的庄稼运不下山,怎么办?老赵和两个弟弟,把拖拉机、脱粒机、大车等农用器具拆散运上山,并以拖拉机作为动力建起来了通向山下“索道”,来回运输物资变得轻松便捷,小日子过得也算是有滋有味。
8月14日记者到来时,老赵刚刚从鸡窝里捡了3个鸡蛋,“山鸡蛋香,我给你们煮煮尝尝……”
小屋旁,老赵自砌3个炉子:“这个做饭,这个炖鸡,这个烧水。”他一边准备煮蛋,一边介绍,熟识驴友来访,他会“狠狠心”杀鸡款待。
近年来,追寻自然风光的驴友增多,大寨以其原始风貌和人文景观,成为“淄博市登山协会训练基地”。周末,驴友纷至沓来。老赵指着远处的“三剑山”和“美人沟”等景点,给记者讲述着,这群山深处的沟壑、高耸的悬崖峭壁,都令驴友流连忘返。
每到周末,来这里的驴友一队又一队。老赵指着远处的“三剑山”和“美人沟”(山上的二处景点)说着,这里群山深处的沟壑、山谷两旁高耸的悬崖峭壁,都巍峨挺拔,雄浑冷峻,让驴友们流连忘返。
眼看着山上的人越来越多,老赵的心思也活泛起来。他就烧些水、做点菜,有时候也会杀鸡犒劳驴友。渐渐的,老赵在驴友圈里越来越有名气,成了大寨寨主,他的石头房子便成了“驴友之家”。
“我最高兴的就是有驴友到来。我们一起做饭,一起聊天,一起喝酒,有时候他们会扎下帐篷住在这里,我们一聊就是一宿,特别放松,特别愉快。”

当然,作为山上唯一的居民,老赵也是众多驴友的指路人,19年间,他已经数不清楚帮多少迷路的驴友带路,就像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山上种下了多少树木一样。
老赵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安家,多次想接老赵下山安度晚年。但老赵舍不得这片山,依然留在这里,坚守着19年如一日的生活,独自一人守在大山之巅,每日修剪树木,巡查归来,种菜喂鸡,怡然自得。
在这方圆几公里的山巅,老赵不仅是优秀护林员、拓荒者,更是大山忠诚的守护者、深情的守望者。“只要条件允许,我就一直在这里,一直守护着。”望着远山,老赵深情地说。
(大众新闻·鲁中晨报记者 王晓明 任灵芝 实习生 刘轩志)
网站来源于网络。发布者:中青网,转转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yxjz.org.cn/25824.html